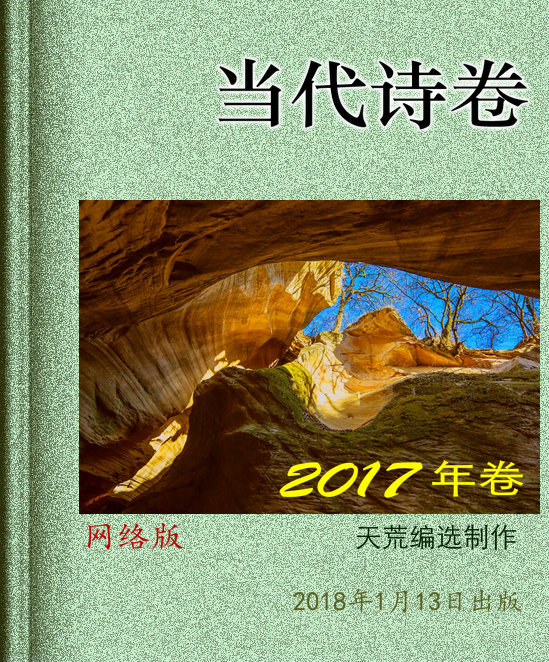
编者说明:本卷资源均
选自网络,有谬误处或
有异议者请告天荒修改
《当代诗卷》投稿博客
blog.sina.com.cn/ziyew
《当代诗卷》投稿信箱
kongxz@163.com
天荒编选制作
2018/1/13
|
|
| |
钟磊
失眠大师(27)首 (阅读989次)
《怀人诗篇》
黑夜当中的青铜太小,变成了圆形的一点儿,
令人挂念,也令人不安。
我在屋瓦连绵之处遇见它,
它在择路攀爬,并且一路问我:“我是不是你身体里另外一个人?”
我不说话,我知道它是一件隐身衣,
在一个良夜里宽衣,又从高空丢下一枚硬币,
在让我的灵肉相对称,我说:“我是一首诗的一个地址”。
我像一首诗的一个空罐子,
摄走了我的魂魄,在让一百个我辨认我,
我却避开了人世的躁乱和拥挤,
牵着另一个我,走过了十步之内的乱世。
2017/10/3
《月亮的自省》
一样的夜,月亮把睡眠挖出一个洞,
在转移我们的头颅,让思想者看见思想的耳朵。
而我们仍在给所有的手指带光环,
指出所欣赏的事物:黑蝙蝠在黑夜里跳舞,在翘臀的一瞬间夹带风,
在放弃乡愁,在美丽的错误中谢幕。
我们也试图从明亮的元素出发,赶在月亮伸出死亡的舌头之前,
标示出一种残留物,月亮却留下了一小撮骨灰,
丢开了一个圆形,丢开了一种趋光性,
也不在乎幻觉的小,在说:“多舌的月亮似一个长舌妇。”
2017/10/3
《病诗》
十字架在阳光中划十字,划成一个叉,
它反而变成了圣洁的反面,在冒充神,在羞辱人们。
十字架妄想虚构一些事,
在拆分罪恶,却分不开腐败和溃烂,
在陵园变成肮脏的诱饵,让一堆堆尘埃睡死过去。
一只黑乌鸦丢开了自己的口臭,蹲在十字架上拼命地呱叫着,
又引来一大群黑乌鸦包围过来,
它们喜欢腐烂的气味,
它们把嘴巴插进人们的灵魂,在十二克的灵魂中加热,
却越来越像一个黑暗的刺。
2017/10/12
《滚滚红尘,你滚吧》
把腐烂的尸体深埋在红尘中,谁的灵魂在枕着它?
鬼神的形迹已经无影无踪,
我也不是我的影子,我在精神错乱中书写一些词,
譬如:十字架不是灵魂的根茎。
我又看见十月的旌旗,在把我的脸遮蔽成阴阳两半,
在相互乞求或掴耳光,在惩治腐败,
像一个人在向人们抛幻觉,在丢下剩余的名利残渣和齑粉。
而我不能接受人神的恩宠,只想坏掉自己,
在荒诞的红尘中把灵魂贴上一个标签:闲人止步。
又缺席于人神的宝座,在报复滚滚红尘,
在以放浪形骸落井下石,又野蛮地吐出一口痰,
在让苍蝇和乌鸦的飞翔在空气中生锈,
在说:“滚吧,滚滚红尘只是一个没有窍壳的皮蛋”。
2017/10/18
《懒慢抄》
阿Q本名叫谢阿贵,活得落魄不堪,
总做些偷鸡摸狗的事,偷过周作人的两块古砖,
被周树人抄写录下来,在《阿Q正传》中揪住谢阿贵的辫子不放,
又逼迫谢阿贵向吴妈下跪。
可怜的谢阿贵,很委屈地在《阿Q正传》中败下阵来,
一下子把别人干的坏事归在自己的账下,
在说:“认了,认了”。
又胡扯一遍说:“先贤说过,恶居下流,天下之恶皆归焉”。
而今,我再扯远一点儿,
干脆给谢阿贵装上第三只手,交给一个厨子剁了,
再给厨子五角或一元钱,
让谢阿贵站在《阿Q正传》中冒充贵人,
或让谢阿贵抱住民国的旧时光,和鲁迅的幽魂击掌,
让谢阿贵说:“我比前世都阔了”。
2017/10/18
《纸罪笺》
如《国朝宫史》所云:凡字纸俱要敬惜。
唐吕洞宾制定了法典,
譬如:以字纸引火打亮者,十罪,生疥癣。
而在如今,我的脸红如传国玉玺,
在把奏折一般的心呈送给诗,
在说:“太阳太肥了,像一个蟾蜍蹲在王朝的祭台上呱呱叫”。
我不妨反问一下,我在《诗经》上度我,
且以字纸把我裱糊成神像,再把我塞在墙壁的神龛上,
可有别功?为何《国朝宫史》不录?
2017/10/20
《我们和灵魂互看,且互诉黑暗》
面对黑暗,很难说出灵魂的样子,
偶尔说出一两句却为时已晚,
以至于在一个封闭的皮囊内,逃入一枚苦胆,
在一道伤口中说出命运的呼吸或等待,却是一滴咸涩的血。
我们睡在诗意的贝壳中,发明了一颗心,
爱上了珍珠一般的记忆,
在一次火葬中飞行,在一种白色里变轻,
经过了十字架的四扇门,骑上灵柩说:“让我走吧,让我走吧”。
灵魂的样子不见了,或是一面镜子,不是,
或是一帧老照片,也不是,
我们根本不是人世的布局,进入了死亡隧道,
靠近了真相的另一边,在变蓝。
2017/10/23
《甲壳虫续编》
我似先知,在雾霾中翻了一下身,
又横卧在有玻璃窗的窗台上,在蹬着无影腿,让人数不清。
像弗朗茨·卡夫卡把自己藏起来,
在冒充甲壳虫一族,辜负了一战的雾霾,
在命里打盹,在宿命中认命,也不肯在宿命里挪动一步。
或在切斯瓦夫·米沃什的影子里穿上一件破风衣,
扑灭了二战的一场火焰,
在用波兰语给天空打补丁,又喝上一口白开水,
再用干瘪的嘴巴说:“见鬼去吧。”
我又突然现身,在中国式的雾霾中再玩耍一次,
穿上一件对襟的中山装,打开窗户,把甲壳虫装进一个小衣兜儿。
接下来,再把它放在书桌上,
打开一盏台灯,让它像晒太阳一样,
或盗用大师的名义,爬上我的铅笔杆,
或冒充自由的嫌疑犯,写下无名遗嘱。
2017/10/25
《旧城小区改造一页》
立冬的时光,流淌了一条街,
沉淀在旧城小区,像泛黄的树叶,自西向北,被大风吹过。
等于旧城小区改造的苍凉,
等于无家可归之地,等于灵魂的无助告白。
忽然,本杰明?富兰林克从7层楼的窗口中探出头来,
在一个黄昏中观看一只放飞的风筝,
仿佛把我看成了时光的流寇,在弥补时光的某种亏空,
又放大了一个市井小民的借口,
落实了我的偿还契约,或与一枚五毛钱的铜色对等。
2017/10/26
《雾霾的梦境》
比如此刻,我坐在阳台上抽烟,
一抬眼便可以看见,雾霾中的烟囱蔓延出一缕焦虑,
比门前的一棵歪脖树还要恐怖,
好像是一个魔鬼摇晃着铁锤,向我猛砸过来。
砸破了我的头,又把我的脑浆吸干,
吓得我的祖母,蹲在阳台一角,
像一个拾荒者,紧盯着菜板上的一把刀,目光冷得像冰,
紧盯着魔鬼把一根手指伸进喉咙,
压下饥饿一词,又在一日三餐的餐桌上下赌注,
在把一个瓷碗当成活命的耳朵,摇晃起来。
2017/10/27
《仅此而已》
仅此而已,灵魂在召唤我,这是必然。
而我却在背叛我,模糊了真相,
恰似在玩自焚,暴露出灵魂,居然被凡夫俗子们看扁了。
我独坐在一面镜子中,
须臾了片刻,又躲藏在镜子的背面,在隐姓埋名,
又带走一个劫数,在蝴蝶的标签上逃脱。
2017/10/27
《哲学的耻辱》
马丁·海德格尔说:“最永恒之物是道路”。
阿巴斯·基阿鲁斯达米说:“我活在现实和幻想之间”。
他们在对着天空说话,在逢场作戏。
我看到了一棵樱桃树在随风摇摆,
树木丢下了樱桃的生育,趋于干燥和颓败,
在把哲学的元素降低,
或相反,在变成一根蜡烛,在让一只蝴蝶围绕火焰飞,
反而让它变成了火焰的一部分。
来不及忏悔,来不及逃命,他们也把我丢在了一部电影胶片上,
在虚构的梦境中捐躯,在用哲学喂养现实的猛兽。
我发现两只老鼠——一只是白的,一只是黑的,
正在啃咬我的骨头,让我在整理好衣冠后,又伸手摘草莓,
却无法找到额头上的铁。
2017/10/31
《又一个矛盾》
请看,夕光和湖水漫上了堤岸,
淹没了南湖的步行街,犹如我的漫游富于启示。
可是,冷风在把我的脸色抽干,
仿佛是野樱桃树上闪光的野樱桃。
我再想象,一丛菖蒲在代替我的双腿,比我的双腿自由,
在湖水中说:“没有你,我并不存在”。
的确,我作为一个过客改变不了什么,我再把菖蒲画成绿色吧,
在抄写色彩的符号,漂浮在空中。
此刻,我羞于接近距离我最近的事物,
在用体内的血代替信仰,在菖蒲的香气中返回无形,
也不担心舌头濡湿嘴唇会把嘴唇的红色抹去,
惟有我的想象归于此在之美。
2017/11/6
《立冬报告》
又一场雨夹雪,倒流在立冬的斜坡上,
有人在为雨和雪编密码,又反弹出十九个意念,
仿佛凿开了冬天的窗玻璃。
有人在说:“猫咬耳朵的日子来到了!”
于是,我在睡梦中有了一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担心,
在让一只猫睡在我的左侧,
让越来越紧迫的日子像藤一样在缠绕某物。
一只老鼠偷走了某物,一只猫追赶过去,
却缺席了一场无辜,在冒充玻璃的重量卡在了窗口上,
在立冬后的第二天说:“智力取消了命运”。
2017/11/8
《乌有之辞》
剪开生死,等于把命剪断。
而我却喜欢把生死抛给你,去追赶乌有之辞。
我接近于飞翔,消失于无形,
一直没有被弯曲的天空反弹回来,被乌有之辞过滤一次,
像黄昏的禅师,盘坐在诗中,
说起含糊言辞,像奇诡的灵魂,缭绕在山水之上被你瞥见。
而在见与不见的对面,仍然不是思想的延伸,
在一首诗之外,你欠下了我的账,
仍在与远方的远方沆瀣一气。
倘若你的乌有略胜过我一筹,在用一粒尘埃记录一种偏差,
我会陪你,用我的一生减掉你的无用,
让我从天而降,留在你的影子里还原成诗。
2017/11/11
《瞧瞧,谁也不知道的》
瞧瞧,一种事物在房屋顶上冒烟,
在回答尘俗的悔悟,在一场火焰中变成人间最长的长叹。
灼热的欲望在返回厨房,
在噼啪作响的厨具上敲打我的肋骨,
在印有云纹的瓷砖上攀爬,在危耸的烟囱上留下痕迹,
在升入天幕之际,描绘色彩的虚无,
或是以幽暗的启示,勒令我放弃多余的修辞,再把我的灵魂带走。
正在晾晒的空衣服,空出了空的味道,
从傍晚的牙缝中间挤出沥青,睡成了死亡的一条街,
如此形成了黑夜,更不拥有肉体,
死神的红舌头在说:“失踪的人在叫喊着救火车”。
我却在用一双手把身体拧干,
让我配得上一场葬仪,在一团火里用一根手指指认灵魂,
在喊:“我要清算人生的债务,摆脱死亡的灰烬”。
2017/11/12
《幻觉重现》
雾霾布满天空,我瞥了它一眼,
它在天空中留下一个比魔鬼抓伤我身体更深的爪痕。
伤口,的确是存在的,
像一只灰喜鹊死在了青年路上,
灰喜鹊曾经活在一丛树林中,活得太渺小了,
以前无人留意,现在也无人留意。
这几乎是二十年间的事儿,天空弯曲了,然后是我弯曲了,
因此,我排列好悲哀或耻辱。
因此,我佝偻着身子致力于描述无人杀死灰喜鹊的全过程,
纠结着雾霾事件,因此研究这一点,
假如我死了,是否关联着一门艺术?
2017/11/13
《谢幕》
忽然,一个日头沉下去,
把我捆绑在暮色的阴影中,在打滑的夕阳上扯谎,
像倒挂在树枝上睡着的黑蝙蝠。
在我的身体两侧,我看见有两个人在肋骨上拔鱼刺,
不皱眉,却摘下两顶黑礼帽,
在问大家:“请思索一下,天空有没有池塘?”
我琢磨了好半天,两顶黑礼帽好像是盛满我和影子的两个小水罐,
好像是我的活命魔法。
2017/11/14
《失败之书》
偏见,在另外一边看我,
而我故意闭上眼睛不看它 ,
在贾岛的书赠同怀人,词中多辛苦中冥想,好像一个僧人,
也好像一个匿名的神,在万万众的人群中秘密地耗散自身。
让我的棺椁在空中飘,带走一具尸骨,
在单边的孤寂中,拿走古墓和刺柏之间的风声。
或许,可以关掉纽扣的微亮,
或许,可以发出一种声响,像闪电,劈开了大地的睡眠,
虽不复身,但也像扫地僧一样举着亡灵书,
点燃三炷香火,在月光中变成不明飞行物,在把禁欲的意义变小。
恰如偏见所愿,让失传的手艺在我的命里显现出来,
顷刻间,滑过了偏见的斜坡。
2017/11/16
《讲故事》
在骨头的裂纹中,有一种嫩芽冒出来,
不是真理,在啃着傍晚的灯花,像一个神话。
有人在追问:“你梦见一朵灯花一样的人吗?”
我不得而知,只记得落日落在草原上,
还没有改变放牧、打草、转场、挤奶、打酥油、捡牛粪……
我坐在一座毡房里点灯,连接好落日的结尾,
在一面铜镜中采集失去的风景,
发现自己易于感伤,在一页经文上颤抖着说:“虚空在吞噬灵魂”。
我却不能信以为真,不能把推想推得太远,
也许我只是一个三位一体的小灵兽,在非我的属地发脾气,
夸大了一种美德,在偏心地描述一丝微光。
2017/11/17
《我的后半生》
记忆的嘴唇趋向概念化,亲吻着灵魂的鸦片,
把我抛弃了,把我变成故事的结尾。
而我在妙笔生花的记忆上复活,喜欢拼接一些小玩意儿,
让约瑟夫·布罗茨基毗邻我的生活街道,
让我执意寻找一种老物件,
把书稿兜儿翻来翻去,寻找一份传世手稿。
似乎是我的影子还在,还在时空中搬字过纸,
还在一行诗里品尝古老的辩证法,
避开时光的剥蚀,吞灭了我的死,再把记忆的链条扣死。
2017/11/20
《荒谬的装置》
忽然,一个影子从一做教堂中跑出来,
其实他是某年某月某日出生的人,
像索弗拉基米尔·洛维约夫在说:“灵魂的兴奋,是谨慎的骗局。”
忽然,还有一个影子在给我用私刑,
让我高喊起上当受骗,又皱了一下眉,
学着勃洛克在说:“无产者是恶棍,同志一词是骂街。”
一晃儿,我回到了1853年和1880年,
站在圣彼得堡的一条大街上,在一块路标上照镜子,
我和我在面对面,却缺席于荒谬的装置。
2017/11/21
《安慰药片》
感冒了,咽喉疼,咳嗽,流鼻涕。
我吃下一粒银翘解毒片,
它的绿色胎衣逐渐溶解在我的体内,在转述我的生活歧义,
在说:“小鬼在显摆着各种小杂什”。
2017/11/21
《昨夜札记》
昨夜的大北风,吹进了清华路的死胡同,
在和牛大人火锅店的炭火顶嘴,
在说:“牛大人不如小人的牛皮大”。
有人借着卖炭翁的嘴巴说:“唐朝不甜,不大于祖国”。
来不及接受烈火审判一场争辩,
店长在给客人们上课,在说:“停电十五分钟,听从牛人安排”。
我听说一头牛死于时间的火焰,
想过去看一看,走上一条大道,
在一张宣纸上画《老子出关》,再让一个书童举着一方朱红印赶过来,
似一个掌灯人,点亮了水墨里的冰。
2017/11/22
《让我来陪死亡玩一把》
黑夜来了,黑色挤在门缝中叫骂我,
逼迫我和它决一雌雄,
我在喊:“让灵魂的样子,把我的样子带走”。
我看见它跑进了死亡的厨房,正在瓜分死亡的尸体,
又溜出了楼宇门,又踏响了后楼梯,
从芙蓉桥的路口,跑进了椭圆形的体育场,在短跑线上疾速奔逃。
正是那黑色,把我卷进了一场火刑,
让我在追赶黑夜的最后一夜,犹如火中取栗。
正是因为这失眠的天空,才让我来陪死亡玩一把,
或让死亡成为帮凶,让死亡让出一条道,
让死不了的天空把我的灵魂带走,
像一个泄露天机的人一样——这才是我的样子啊!
2017/11/23
《失眠大师》
一双眼睛混淆了夜,四片天空飘起来,
恍惚间,一群野狗抬着一具死猪的尸体从南山上走过来,
被一个猎人打击,子弹在飞。
忽然,我惊醒过来,在寻找一只笼子,
想在天亮之前把它挂在天上,寻找一只鸟儿,
让死亡的门槛低下来,去交换猎枪,
再把死猪的尸体抬出去,埋葬一场灾难,之后,天空渐渐亮了。
幸亏我没有销毁一个失眠的现场,
幸亏我在骤变的现实中,把失眠的大师关在一个房间里,
让我平躺在一张床上,呆望天空三天,
然后,学着卡夫卡说:“我又跟自己说话了”。
然后,写下11月10日。床。恶是善的星空。
然后,写下12月4日。宰猪。
2017/11/24
《皇上的口袋》
北平的北被黑色掏空了,
装在皇上的口袋里,像一个不知廉耻的人。
列夫·托尔斯泰说:“手心冰凉。真想哭,真想爱”。
我明白他说的意思,
我是他的老相识,写一封回信吧,
让一个小邮差转述我的意思,说在北平以北我还活着,
在中国的一个小城镇中练习隐身术,
像一个独行客从祖传的秘笈里跑出来,又从皇上的口袋中溜走,
不依赖于皇上的手心活着,
还会和皇上说:“我们各活各的”。
2017/11/27
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 [关窗口]
| |